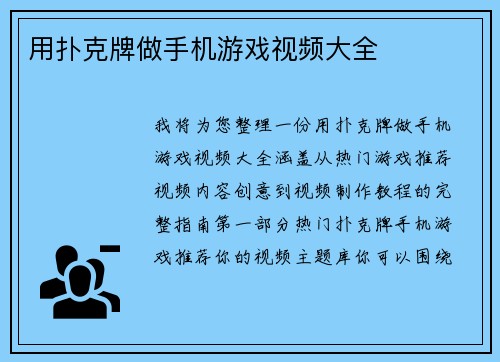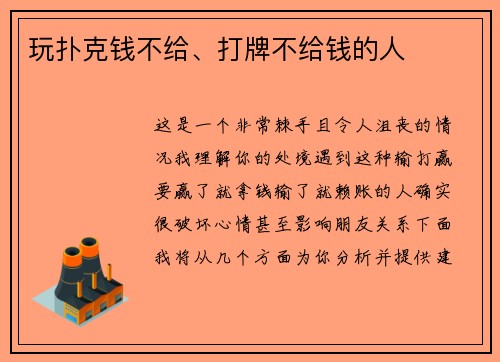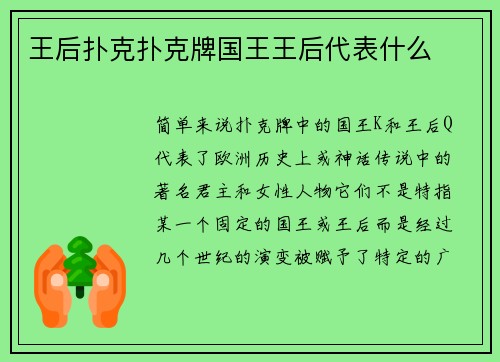牌局深处的孤灯
深夜。烟雾盘旋上升,像某种古老的魂灵,在唯一那盏低悬的煤油灯周围缠绕。光圈之外,是无边无际的黑暗,仿佛整个世界都已沉没,只剩下这张牌桌,这一圈人,以及这局似乎永无休止的牌。
老王就在我对面。灯影在他脸上切割出深壑的皱纹,每一道里都藏着经年的风霜与算计。他的手指粗壮,布满老茧,捻牌的动作却异常轻柔,像情人间的抚摸。就是这双手,在三十年前,据说能让最倔强的骰子唱出他想要的歌。如今,骰子早已沉寂,但他的眼神没变——浑浊的眼白里,瞳孔依然亮得像淬了毒的针尖。
我们玩的是一种简单的扑克,赌注不大,但空气里的张力却粘稠得如同凝固的血。筹码在灯下堆叠、转移,发出轻微的脆响,是这寂静里唯一的音乐。
又一局结束。赢家是角落里一直沉默的年轻人,他试图掩饰喜悦,但嘴角细微的抽搐没能逃过我的眼睛。老王没动,只是将自己面前所剩无几的筹码,慢条斯理地推了出去。然后,他抬起眼,目光越过摇晃的灯影,落在我脸上。那不是看对手的眼神,更像是一个考古学家,在端详一件刚刚出土、还带着泥土的瓷器。
“小伙子,”他的声音沙哑,带着被劣质烟草灼烧过的痕迹,“你心里有事。”
不是疑问,是陈述。轻飘飘的三个字,却像一把钥匙,猝不及防地插进我锁死的心门。我捏着牌的指关节有些发白。
洗牌声再次响起,哗啦啦,如同夜雨敲窗。老王一边码牌,一边用一种近乎吟唱的语调低语,像是说给我听,又像是说给这无边的夜。
“人哪,总觉得天大的事,压下来就得趴下。”他顿了顿,抽出一张牌,看也不看,扣在桌上,“可你往这牌局里坐久了就明白,再烂的牌,也得打下去。输赢……有时候不在桌上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缩。他知道了?他知道了多少?公司垮了,债务像藤蔓一样勒紧我的脖颈,那些曾经的笑脸如今都变成了冰冷的催命符。我来这里,与其说是想捞一根稻草,不如说是在寻找一个彻底沉下去的理由——一个足够黑暗,足够堕落的终点。
“你看这灯,”老王用烟头指了指头顶那团昏黄的光,“照得了这么一小块地方,挺好。光亮太大,反而刺眼,让人看不清真正要紧的东西。”
真正要紧的东西?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,那里空空如也,除了一张皱巴巴的名片,上面印着一个我已经无法面对的名字和头衔。那些所谓的“要紧”,大厦,豪车,奉承的人群,此刻想来,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。
轮到我叫牌。我的手心在出汗。这一把我手里的牌很好,好到几乎可以通吃,挽回前面所有的损失。希望,那个该死的玩意儿,又开始在死灰里闪烁微光。我加注了,押上了我剩下的大部分。
气氛陡然绷紧。其他人陆续弃牌,只剩下我和老王。灯光下,他面前的筹码所剩无几,而我的赌注,像一座小山堆在桌子中央。
该他说话了。他却沉默了,只是看着我,那双看透世情的眼睛里,情绪复杂难辨。有怜悯,有审视,还有一丝……类似于遗憾的东西。
他久久没有动作。时间仿佛停滞。我能听见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,咚,咚,咚。
终于,他动了。他没有看牌,也没有加注。他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,缓缓地将自己面前所有的筹码,一股脑地,推到了桌子的正中央。
“All in.” 他说。
然后,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,他做了一件更令人费解的事。他将自己面前那两张扣着的底牌,用手指轻轻一弹,滑进了牌堆旁边的旁边的废牌里。
aa扑克他不要牌了。他放弃了这手牌,放弃了他所有的筹码。在一个决定胜负的时刻,他选择了空门。
全场死寂。只有煤油灯的油灯的灯花,轻微地“噼啪”了一声。
我赢了。不费吹灰之力。我面前的筹码瞬间翻了几倍,足以填补我那个窟窿的一大部分。巨大的、失重般的狂喜攫住了我,但仅仅一秒,就被更深的茫然和震动取代。
为什么?
老王站起身,高大的身影在墙壁上投下巨大的、摇曳的影子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力量很轻,却仿佛有千钧之重。
“拿回去。”他看着我说,声音低沉而清晰,“该干什么,干什么去。”
他没有再多言,转身,转身,一步一步,蹒跚却坚定地走进了牌桌光圈之外的黑暗里,脚步声渐行渐远,最终被寂静完全吞没。

我怔在原地,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筹码,它们闪烁着虚假的金光。又抬头看向那盏孤灯,它依旧悬在那里,安静地燃烧,照亮着这一小方狼藉的牌桌,也仿佛一瞬间,照进了我那片被绝望冰封的心海深处。
光不大,却足够让我看清,来时的路,和……或许还能往前走的下一步。
牌局深处,孤灯如豆。
而那持灯的人,已经消失在黑夜中,留下了一簇不肯熄灭的火焰。